不过,马克思对于自由问题的深入探讨,离不开早期对政治自由的关注;而且,这一时期马克思所形成的思想探索、理论成果,也并没有因为他的“两个思想转变”而归于终结,而是构成了他进行资本主义批判、构建人的解放学说的思想起点。因此,有必要回到文本的原初语境,结合近现代思想史的演进,重新探究马克思早期分析政治自由的理论场域,厘清其特质,进而搞清楚马克思对其中张力、矛盾求解与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无论是对于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还是对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和特性,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马克思之前的政治自由观念:从霍布斯到黑格尔
马克思对于自由的理解受到德国观念论传统的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马克思早期思考自由问题时的基本向度都来源于德国观念论的规定。这种规定性明晰地体现为,马克思对自由问题的探索同样是从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之中出发的。而这种“应然与实然的矛盾”本质上即为人的理性思想活动的指向与人在社会现实中维持生存的需求之间存在的深刻张力。显然,这一思想内容可以确凿地上溯至英法两国政治思想家对于“契约论”的探讨之中。因此,在论述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政治自由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一思想史内容进行厘清。
在社会政治思想的谱系中,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概念先出现在霍布斯论述“臣服契约”的前提之中。在这里,自由从属于“自我持存”的观念,即“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在这一理解下,霍布斯推导出他的结论:人们必须放弃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并且要将这些权利让渡给“集体”,从而换取“集体”对他们生存的保障 。不过,霍布斯也认为,个人牺牲权利以换取自我持存的行为是面向国家的,就每个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则是“每一个人都放弃了防卫他人的权利,但却没有放弃防卫自己的权利”。因此,在霍布斯的思想中,自由概念具有生存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双重样态,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由,需要放弃自己的政治自由。
换言之,在霍布斯的国家学说中,现代国家实现的同时就意味着人的政治自由被取消。卢梭激烈地反对这一观念,在他看来,“契约论”所要实现的社会和政治形态,是“一种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的结合形式,使每一个在这种结合形式下与全体相联合的人所服从的只不过是他本人,而且同以往一样的自由”。并且,在这种社会和政治形态中,“由于每个人都是把自己奉献给全体而不是奉献给任何一个个人,由于每个人都能从其他结合者那里得到与他转让的权利相同的权利,所以每个人都得到了他失去的东西的等价物,并获得了更多的保护其所有物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卢梭将对人类本质的理解从“自我持存”转换到为了“自由”。他指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做人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一切的人来说,是无须给予什么补偿的。这样一种放弃,是同人的天性不相容的。剥夺了一个人行使自己意志的自由,就等于是剥夺了他的行为的道德性。”因此,既然人类不可能为了保存自己而放弃自由,那么自由和国家的学说就需要从相反的方向进行建构。
进而,卢梭提出了自己的自由概念:“加上得自社会状态的道德的自由;只有这种自由才能使人真正成为他自己的主人,因为,单有贪欲的冲动,那是奴隶的表现,服从人们为自己所制定的法律,才能自由。”也就是说,自由不仅意味着人规定自身行动法则的自主性,还意味着人将这些法则强行加诸于自身时所体现的自律性。因此,自由即是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在此种阐释下,政治自由的本质即在于个人的“私欲”能够转化成合法的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威才有义务服从”。在卢梭构造的公民社会概念中,这种政治自由的呈现就是“公意”。“公意”反映了社会中一切个别意志的普遍化,并且是一切个别意志转化为全体普遍欲求的“系统”。易言之,在这种“公意”系统中,如果一个人的意愿能够被所有人所意愿,那么它显然是被普遍肯认的;如果一个意愿得到了普遍肯认,那么它就一定是“道德”且“自由”的,因为它超越了“私利”的范畴。因而,这种“公意”所缔造的是一种纯粹形式化的自由原则,其根本功能在于为政治提供合法性依据。
康德将卢梭的自由概念进一步凝聚成一个概念:人为自我立法。对于康德而言,自由即是理性的最高点:“自由概念的实在性既然已由实践理性的一条无可争辩的法则证明,它就构成了纯粹的、甚至思辨的理性体系的整个建筑的拱顶石。”而哲学的最终任务则是“将一切都从属于自由意志”。但是,康德的自由概念也是纯形式化的。康德用这样一个“诫命”来表述其自由概念:“这样行动: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 而这种自由,“不能在他所处的世界环境中寻找,而是完全要先天地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去寻找”。由此,康德的自由观念虽然具备强烈的道德感和现实批判意义,却是空洞的“应当”,并难以在此岸世界中获取内容以充实自身。
不言而喻,卢梭和康德的自由事业是一种“纯思”,而在他们规定下的自由概念虽然在道德哲学的层面达到了顶点,却难以在现实中被落实。事实上,无论是“公意”还是“自我立法”,都难以在政治实践中予以贯彻——基于“公意”的自由蜕化为一种集权主义的观念 ;“自我立法”的根本目的也不是约束“现实的人”,而是形成“法则”,对人的认同和尊重也让位于对“法则”的“敬重”。
自由作为最高的普遍性,在社会现实中只剩余形式的外壳和抽象否定的本质,沦为政治家进行操纵的工具。黑格尔发现了这种形式自由观在现实性方面的软弱,更指出其内在逻辑上的矛盾:对形式自由的追求反而造就了否定自由的消极后果。这是因为,既然形式自由的目的是普遍性的,但最高的普遍性即意味着对一切特殊性的夷平,那么彻底的自由就意味着两个后果:自由将一切内容都纳入其概念之下,使自身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实体;或者,自由失去了实体的内容,仅余一个空洞的符号外壳。当然,对于黑格尔来说,绝对的内容等同于无内容,以上两种自由的样态都是他无法接受的。
在评述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历史意义时,黑格尔进一步批判了这种形式自由观,他指出,自由的否定性力量源于对形式的推崇,因为“否定自由的自我意识正是从特殊化和客观规定的消灭中产生出来的”。而这种自由“不能达成任何肯定性事业,它既不能达成语言上的普遍事业,也不能达成现实上的普遍事业,既不能完成有意识的自由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也不能完成有意识的自由所实现的行动和事业”“它所能做的只是否定性的行动;它只是制造毁灭的狂暴”。
在黑格尔的思辨逻辑中,自由之本质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是“经过在自身中反思而返回到普遍性的特殊性——即单一性”。也就是说,自由的发展必须在经历普遍性环节和特殊性环节之后,于单一性环节之中才能得到实现。而在单一性环节中,自由“除了与它自身相关外,它不与其他任何东西相关,从而对其他任何东西的一切依赖关系都取消了”。那么自由以及通过自我规定以求抵达自由的努力,实质上都是自由本身,自由于是又回复到了普遍性的维度上,作为一种“内在的必然性”而存在。对于黑格尔而言,自由唯有经历过如此演绎,才能具备实体性的内容,进而超越形式自由和有限自由,从而成为具体的、理念的自由。而在现实层面,“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换言之,国家是以普遍性原则为主导的家庭和以特殊性原则为主导的市民社会的内在目的。在这一层面,黑格尔式政治自由的内在一致性最终显现出来:“自由的普遍即个体的支点,这种个体性也摆脱了全体所共享的认识,不是由全体所构成。” 黑格尔意义上的政治自由的主体是意志,本质是精神主体性,其所要求的是自由作为必然性而得到彻底贯彻,至于其外化形式则不在考察的范围内。因此,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总是在深入批判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做出巨大程度的妥协——无论是耶拿时期他对权力必须集中于某个个体手中的论证 ,还是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君主制和专制主权的辩护,都清晰地显示出这一特征。由此,无论是黑格尔早年便已提出的“真正的自由共同体”命题,还是后来的“现代国家”理念,都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概念。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霍布斯到卢梭的契约论传统,还是卢梭—康德式的自由法则概念,抑或是黑格尔所发展出的“具体的普遍性”的自由观,都在回应现实的政治自由问题上陷入困境。这种困境也呈现出现实政治的局限性,即要么牺牲部分自由权利以换取对“更高”的自由内容的保障;要么尝试通过抽象的形而上学解决方式来实现自由,最终忽视了具体的社会现实。但值得肯定的是,虽然这些理论家们所提出的自由方案在理论或实践上存在种种缺陷,但他们的努力使得政治自由得以成为一项问题,并使这一问题的问题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得以大致澄清。这为马克思开启对相关问题的探索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政治自由的必然形式:“最高共同体”中的自由
在博士论文《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就展现出了对自由问题的强烈关注,并将自由作为自己立论的基本立场。但直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面对“物质利益难题”之后才开始真正对政治自由问题进行审视。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马克思指出:“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这一理解显然指向的是卢梭—康德式的自由法则概念。但马克思也发现了这种形式的自由在现实政治中所遭遇的困境:“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对林木盗窃的立法本身进行了猛烈批判,他指出:“难道无视法律的东西能够立法吗?正如哑巴并不因为人们给了他一个极长的话筒就会说话一样,私人利益也并不因为人们把它抬上了立法者的宝座就能立法。”
显然,马克思之所以如此抵触这种形式的法律对私人利益的维护,是因为他对卢梭“公意”理论的接受。因为保护林木的私人利益并没有转化为“公意”,那么对其进行立法显然是违背了立法自由的要求的。但是,这种状况却成为社会的现实,并且,被“契约”委托来进行立法的机构的行为还在使这种现实愈发牢固。存在于社会中的矛盾不仅没有走向和解,反而更加深化。这一矛盾演绎深刻撼动了黑格尔国家观念的根基——私人利益的矛盾不仅没有在国家那里得到扬弃,国家还反而成为私人利益实现和保存的场所。具言之,《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面对新闻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等现实问题之后,发现了理性自由观念与具体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冲突,而进一步考察的结果,则是发现了理论内部存在的二律背反问题。这促使马克思开始对此前所接受的观念进行“清算”,在明面上是对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实际上隐藏的思想线索则是对卢梭—康德式自由观念的反思。此即马克思构建自己政治自由学说的开端。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通过对宗教、政治和市民社会的三重批判,指出了社会现实中政治自由的虚假性质——这种政治自由是一种有限性自由,是“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这一权利的实现和展开所造就的并非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是“承认构成这种人的生活内容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不可阻挡的运动”。这种“运动”将人进一步塑造为仅有利己本能的人,并且,“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这当然导致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生存状态,即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并且,既然这种政治自由绝非真实的自由,但市民社会中的个人却将其“想象”为自己的自由,并以此为目标不断地实践。那么,最终的结果显然是人的自我异化。换言之,这种以私人利益为根本目的的政治自由,就是市民社会中个人自我异化的政治表达。
马克思认为,造成这种异化现象的根源是现实中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单纯的政治解放的限度在于:“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所谓的自由国家当然将宗教自由包含在内。但是,从抽象的角度来看,宗教所呈现的不过是人的一种特殊化。那么,宗教自由所实现的也不过是对一项人的特殊规定内容的保护。因此,宗教自由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人的真正自由。因而,只要政治自由还在以这样的形式进行表达,人就无法从特殊的规定性中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自由。宗教问题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化的表现,其所反映的恰恰是现代社会内部所发生着的广泛分裂。因此,马克思指出,“犹太人问题最终归结成的这种世俗冲突,政治国家对自己的前提——无论这些前提是像私有财产等等这样的物质要素,还是像教育、宗教这样的精神要素——的关系,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
进一步讲,马克思将这种政治解放不彻底的原因归结为启蒙运动所宣扬的人权概念的内在局限。马克思以《人权宣言》和美、法两国的宪法文本为内容进行分析,指出这种“人权(droitsde l’homme)”并不是普遍的人的权利,而是市民的特权。这是因为特定的历史的人被划分成了“公民(citoyen)”和“市民社会的成员(bourgeois)”。诚然,“citoyen”是一种政治人,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但“bourgeois”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具有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么?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误认。资产阶级人权的症结就在于其将“bourgeois”这种“利己的人(homme)”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但在社会现实中,他们又需要“citoyen”的概念来构造其资产阶级法权,让私人进入公共领域。于是,人的概念就被分裂了:“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 citoyen[ 公民 ] 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通过这种分析,马克思直指资产阶级政治解放革命的内在局限性:它没有实现“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
因此,在《论犹太人问题》第一部分文本的最后,马克思抛出了他对于人的解放的理解:“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在同一时期的私人通信中,马克思则更加直接地阐明了他此时对这种解放所达及的自由的认识:“首先必须重新唤醒这些人心中的人的自信心,即自由。这种自信心已经和希腊人一同离开了世界,并同基督教一起消失在天国的苍茫云雾之中。只有这种自信心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崇高目的而结成的共同体,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
易言之,自由就是人的本质,也是马克思吁求解放的目的。解放的进程意味着人与其自身本质的相遇,这要求将人从各种特殊的规定性中解放出来,进而把人从一个“已规定的概念”中解放出来。这一过程不仅要求在现实中完成对人的存在的社会性构造,更要求在人的观念中彻底地形塑起自由的意识。在这之后,人的个体自由才能通过“外化”而呈现于世界图景之中。
总的来看,经过对“犹太人问题”的分析,马克思显然意识到了主权国家理论和人权理论的结合的现代性后果,那就是主体的分裂和人的政治抽象化。从当代的理论视角对此进行重新审视,马克思在人权与自由的概念被 20 世纪的民族国家政治实践彻底扭曲异化之前,就洞见了生命政治化的现象和结果。但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的局限性也在生命政治的维度上暴露出来——马克思最终仍将解决矛盾的出路归结到人的解放和真正自由上,而问题恰恰在于,马克思将这种自由的实现场域“设定”为在“民主的国家”之中。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马克思对自由的要求是实现人的规定性的统一,即使单个人的一切特殊规定性与“总体人”的一般规定性相统一,从而将人的本质力量和本质属性解放出来,使人的政治性统一于人的社会性,最终在“民主的国家”中实现人的本质力量与人本身相统一。那么,这种“民主的国家”在逻辑和抽象内容上就必须实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彻底统一,否则便无法消解其内部所存在的矛盾张力。而以这种方式呈现的“民主的国家”在实际上就是黑格尔国家哲学意义上的“最高共同体”。而维系于这一载体之上的自由需要一种规定性以获得具体性,否则它就更大幅度地回退,成为康德式的形式自由。但这种对规定性的需要反而说明了这种自由的特殊性,其还没有上升为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因而不是“最高的自由”和“真正的自由”,只是“最高的共同体”中的自由。按照马克思的构想,在“真正的自由”中,人的政治性才统一于人的社会性。那么,在“最高的共同体”中的自由范畴内部,政治性和社会性依然是分离的。因此,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所吁求的自由仍具有政治的规定性。故而,这种自由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自由,被寄托于“最高的共同体”中以实现其形式。
政治自由的内在张力:理性指向与现实需求的矛盾
正如马克思通过宗教和政治批判所展示的那样,理想的民主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事实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利己的人”和“真正的人”的区分即是这种矛盾的最集中呈现。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所想实现的政治自由,是个人得以作为一个理性的公民得以在作为最高的共同体的国家中过着理想的生活。这种“理想的生活”,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就是“摆脱政治桎梏同时也就是摆脱束缚住市民社会利己精神的枷锁”。换言之,政治自由的目的就是实现“类生活”,即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人类有意识进行的理性的社会性的生活。因此,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看来,虽然市民社会中的人所过的是“真实生活”,但这只是基于自然经验且为利己本能所驱动的,远远达不到“理性”的程度。故而市民社会中的人无法实现自由,在将市民社会精神理解为人的本质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无法实现自由。
既然理性的普遍性还不能达及市民社会生活的领域,那么对于理性的要求只能转向国家那里寻求。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显然认同这一观点。在与卢格的通信中,马克思提到:“至于谈到现实的生活,那么正是政治国家,即使它还没有自觉地充满社会主义的要求,也以它的一切现代形式包含着理性的要求。”但是,正如前文已经论述了的,即使“国家积聚了理性的各种规定性:反思性、必要性和普遍性”,其在社会现实中的样态仍然不是理论上的那个“最高的共同体”。因此,国家的理性精神无法超越市民社会的利己精神,国家的形式也不可能摆脱市民社会的要素。换言之,国家的形式奠基于市民社会的范畴,它同样也“继承”了市民社会的痼疾。从抽象的内容层面来说,就是无论哪一项规定性得到了怎样的价值评价,其都作为自然状态而保存在国家的形式中。那么,造就市民社会内部矛盾与冲突的诸种规定性也留存于国家内部,并继续冲突而演绎着。这样下来,国家表面上对于矛盾的“调和”于其实质而言就是一种“掩盖”。在国家中实现的政治自由并没有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本质”,只是成了维系整个共同体的纽带,不断承受着共同体内部矛盾的张力。
马克思就是在这种矛盾中揭示“法国大革命式”政治革命的局限性的。“政治革命把市民生活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但没有变革这些组成部分本身,没有加以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政治革命的目标是在最大限度实现个人自由的同时,保留旧制度中最现实的内容以作为新社会的支撑。也就是说,政治革命清算的是个体之间的关系束缚,而不是个体的本质。于是,“不合时宜”的等级制封建关系就这样被击碎清算了,人的“政治生活”和“真实生活”之间的暂时性的纽带也随之解体了。但是,人总需要新的纽带来维系其社会性存在与社会性实践。故而,私有制被提上了表面,成为新的对人的规定性。资本主义政治理论则将其称为“自由”。在“私有制等于自由”的观念下,政治革命“把市民社会,也就是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看作自己持续存在的基础,看作无须进一步论证的前提,从而看作自己的自然基础”。于是,市民社会就经由政治革命而进入了“理性国家”之中。
但是,政治革命并不认为市民社会是历史的结果。因为市民社会所承载的是人的自然状态,是人仅凭本能而生活的样态,这种生存状态缺乏反思性,故而不是“理性”的。在马克思之后,马克斯 · 韦伯用“合理性原则”的概念重释了理性和自由的观念:自由意味着人能够将行为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一种目的论意义上的合理性。显然,市民社会中的人总是力求“掌握自身”命运的,但其始终受诸因素的制约,特别是他者的制约。这是因为“利己本性”让个体都陷入了霍布斯所描绘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但是,“利己本性”所指向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是人“自我持存”的真实所需。那么,市民社会中基于人而呈现的矛盾,实质上就是理性实现的要求指向和现实生活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对于这一时期的马克思来说,理性是必要的和普遍的,因为“理性向来就存在,只是不总具有理性的形式”。而需求则是经验的、偶然的和特殊的,源于“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上升到政治生活中,这种理性指向和现实需求的矛盾就呈现为公民和人的分裂。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这种矛盾,反而,由于资本主义政治解放对于自由本质的误认,理性指向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被进一步激化了。但是,在人的存在的维度上,人和公民、理性和需求之间又是辩证地联系着的。在现代政治国家中,人只有经由公民的形式,才能自由地在国家的共同体中实现私人的利益。而一个彻底意义上的、理想的公民,其合理、自由的行动也必然是为了实现需求的目的。因此,理性指向与现实需求双方相互依赖又彼此对立。
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理性指向与现实需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认为这种矛盾将使人重新陷于被支配的境地,那就是:“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因此,马克思寄希望于一种政治革命之上,力图实现一种政治的自由。但是,这种革命形态,于其本质而言,是力图实现理性形式对经验内容的介入和支配。这种介入和支配不是为了调和理性指向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而是为了让理性彻底普遍化进而成为需求本身。显然,这一目的无法在现实中实现,于是理性就开始将自身从现实中剥离。进而就呈现出如此的现象:理性放任需求,任凭其以非理性的样态在经验世界中席卷。甚至,在“理性”的政治生活中都被需求所渗透了:幸福这一非理性的内容成为公民向国家所要求的责任内容,并成为一种自然状态而被接受。因此,政治革命所指向的,仍然不是人的自由全面解放的社会现实。对于此时的马克思而言,其还没有直接地认识到政治革命的局限性,但这或许已然构成了他思想中的隐性线索,因为不久之后他就提出了一种彻底的人类革命观念,并即刻投入革命的实践之中。
总而言之,在政治自由的内容中,理性指向与现实需求的矛盾本质性地存在着。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这对矛盾范畴所产生的张力都“撕裂”着自由概念本身,并进一步导向了对政治革命的否定。但是,矛盾的张力同时也是动力,这种矛盾最终所构成的,是革命的动力和现实基础。
政治自由的实践本质:革命的道义论基础
在马克思之前,政治哲学所关心的内容主要是人与国家之间的服从关系问题,即人何以服从于国家、以何种方式服从于国家。在各种学说的反复探索之下,“理性”的路径最终被开辟出来,成为建构这种臣从关系的基点。于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被大致固定下来:个人牺牲部分权利以向国家服从,而国家则为个人的生存以及其他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也就是说,一种社会现实,经过观念上的转化而成为理论上的必然性。理性和自由,就是为这种社会现实所作的哲学辩护。经过法国大革命的“启蒙”,现代国家的责任内容显得更为具体——国家需要实现其所“庇护”的每一个个人的幸福生活,并且,这不是一种承诺,而是一种“应当”的功能。于是,个人向国家服从的正当性被国家实现个人幸福的功能所证明。而当国家不能履行其功能时,服从的理由就成了革命的理由。这就是传统资本主义政治革命的基本原理。
这种传统的革命观念事实上是由洛克所确证的。与霍布斯一样,洛克也认为人最初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中,国家和政府则是为了适应历史和现实而产生的一种“人造状态”,人为了实现“自我持存”需要向国家让渡部分权利。但洛克与霍布斯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洛克所理解的“自然状态”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自由和谐相处的状态,而不是霍布斯所认为的斗争状态。因此,两人所形成的“社会契约”存在根本性的区别:霍布斯提出了一种“臣服契约”;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实际上是对个人权利的原则性确认,进而形成了对君主独裁体制的反思和批判。因此,洛克对国家和政府提出了要求——“政府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这一宣言与其他政治学说的区别在于,其将国家的任务或者目的转回了内部,因而也间接地提供了革命的目的论基础。换言之,洛克论证了革命和解放的目的是实现人类的幸福。在批判奴隶制之不合法性时,洛克的观点可以得到更清晰的呈现:“这种不受绝对的、任意的权力约束的自由,对于一个人的自我保卫是如此必要和有密切联系,以致他不能丧失它,除非连他的自卫手段和生命都一起丧失。因为一个人既然没有创造自己生命的能力,就不能用契约或通过同意把自己交由任何人奴役,或置身于别人的绝对的、任意的权力之下。”这实际上是在叙说现有的制度造成人的生命权利被否定的样态,因而这种制度缺乏合法性基础,故而需要对其加以改变。于是,一种以“人类命运关怀”的形态而呈现的革命话语出场了,其笼罩着强烈的道德光环,进行模糊的目的论承诺。然而,这种革命内部已经先验地蕴含着失败的因素。因为个人进行革命的动力来源于国家的不合法,那么,一项隐含着的内容就是个人应当对合法国家履行服从的义务。相应的后果便是:在“是否进行革命”的判断尚未作出之际,一个新生国家的雏形就出现在要“革命”的人们的观念之中。也就是说,在尚未推翻自己所不满意的国家统治之时,“革命者”们就已经准备好服从于一个“新生”的国家的统治。这就是为何在社会历史中,传统的“革命”模式只能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历史周期律”,而无力跳出这种循环。
康德和黑格尔显然不满足于这种革命目的论,并且发现了这种革命背后的功利主义实质。在他们看来,这样的革命是空洞且非理性的,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为了革命而革命。于是他们重新回到理性的路径开始探索,得出了个人需要将服从国家作为一种职责的结论,也就是说,将个人服从于国家的社会现实转化为一种个人道德上的自我责任。毫无疑问,这种结论是保守的,并让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失去了合理性基础。
对于早期的马克思来说,理论和现实都面临着深刻的困境,自由更隐藏在天国的苍茫云雾之中。因此,为了改变现状,马克思不得不重新审视革命实践的可能性。在康德和黑格尔的影响下,马克思在其早期思想历程中同样是从本质论的意义上去看待理性的。那么,自由作为自我规定的理性的实现,在现实实践之中本来就构成了目的。于是,对于革命的实践而言,其从人的权利转变为人的义务。因为经过这种理论转变,自由已不仅是对当前现实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判断,更是确保理性得以充分行使的条件。由此,自由成为一种绝对价值和要求,其对国家和政府而言,是实现理性的政治的条件。而理性的政治的真正意义在于,其要求国家独立于其所保障的各种自由的应用结果。换言之,幸福、自我的实现、人的尊严等自由的结果,是国家的义务内容,因而国家不应要求人牺牲自我的权利而换取公民的身份。从这一意义上讲,革命获得了新的合理性基础:基于自由这一绝对价值,人不仅有权利规定自我,还有权利获得他人的尊重;如果当前的政治无法实现这一要求,其就应当被推翻。
换言之,革命是扫清理性发展道路上一切障碍的手段,它是方法,不是目的。这是革命的道义论基础。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基于对宗教的批判阐释了革命的原理,“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正如前文所论述的,理性指向与现实需求的矛盾构成了革命的原初动力。那么,而对革命之合理性的“哲学辩护”则由自由的概念所完成了。在马克思思考革命权利根源的初始,这种自由在他的观念中还只是一种政治自由,理性指向与现实需求的矛盾本质上是道德法则与经验内容的冲突。康德认为,现实需求可以通过“法”来服从于理性指向。但马克思认识到了:“在这个自私自利的世界,人的最高关系也是法定的关系,是人对法律的关系,这些法律之所以对人有效,并非因为它们是体现人本身的意志和本质的法律,而是因为它们起统治作用,因为违反它们就会受到惩罚。”因而,通过革命达及政治自由的实践于实质而言就是确立一套实现道德法则与经验内容相统一的规范模式,这意味着“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将被消除”。
但是,这种政治自由也面临着深刻的内在困难,那就是它在从一项观念转变为具体的社会现实时,必然面临着阻碍。正如资本主义在确立其基本政治形式时,也以“自由”作为基本的目的论承诺之一,但是,其社会现实却是只能让“利己的人”获得理性和现实双重需求的满足,而“人”则被抛却在合理的生活形式之外。换言之,政治自由往往只能以一种形式自由的样态呈现于社会之中,而正如前文所述,在形式自由的社会中,自由的理想与自由所服务的真正目的相分裂,生活不是在现实中通向合理性,而是颠倒过来,在观念中实现理性的要求。因此,政治自由之本身也是存在缺陷的。即使现实确实如斯宾诺莎所构想的那样,“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这种自由的框架也无法达及现实的生活,故而需要进一步的革命以实现真正的自由理想。
结语
自由作为近代以来哲学的核心问题,其内涵与意义被哲学家们以显著区别的方式和原则予 以理解。但总的来看,就如汤姆·索雷尔(Tom Sorrell)评述斯宾诺莎的自由观时所言:“有些时候,自由关系到一种对激情的完美主义式的理性摆脱;在另一些时候,它关系到理性与非理 性者的确定权利在事实上的不可剥夺。”在这一意义上,政治自由的概念本身就是消极的,因 为它的实现必然要求强制性、约束性和否定性作为内容。于是,政治自由往往也是抽象形式的 自由而非具体的自由,因为它本质上要求人们保留有否定“非自由”的权利,而不是要求人们使用和实现自由。显然,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政治自由概念和这种消极式政治自由是存在显著区别的。马克思所要求的政治自由,是具有具体内容的、真实的自由。但在对社会现实进行具体分析的过程中,一项内在的冲突也逐渐浮现:若不变革现存的社会关系,那么对自由的追求终将沦为形式的自由。马克思很快便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通过重构理性和需要之间的关系来阐明革命的必要性。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理性和需求的概念都经由革命而得到“修正”并相统一于理性生活的实践之中。这就是说,革命实践的理想是将“对理性的要求”的完成与革命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意味着革命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包含着革命政治行动的理性生活实践也是合理的。无产阶级就是进行这种革命实践的“代言人”,他们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因为自由的概念而具备最基本的内在合理性和普遍性。按照阿伦特的观点,马克思的政治自由观最终可以凝聚为这样一个命题:“无人能在奴役他者中获得自由。”马克思所强调的政治解放的积极意义即在于此——将人从实在的、人格化的具体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显然不仅限于这一面向。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政治解放并不能真正地赋予人自由,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下所实现的政治解放并不能实现人的彻底自由?经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学研究后,马克思认识到:“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自由并不仅仅是政治参与的承诺和权利关系的保障,自由更有其现实物质根基。而资本主义民主所要求的政治自由割裂了这两部分内容,于是政治解放所带来的只是表面的自由,现实中的人仍然受到“物”的统治。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这种“物”的统治的实质:它是资本以客观的生产关系为形式对人进行的统治,是非人格化的抽象统治。马克思指出:“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么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因此,正是这种非人格化的统治从根本上造成了人的不自由境地。而要克服这种抽象统治,就需要变革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社会“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这就将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要求从政治领域拓展到社会领域、从公共性深入到个体性。
因此,就思想本身的演绎逻辑来看,政治自由概念本身的不足促使着马克思探索新的实现人类解放的形式。而通过跳出政治形式的框架并对其展开批判,马克思实际上获得了无产阶级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基本原理,这就是将自由作为革命的道义论基础,毕竟“只有用自由才能为人性的崇高来辩护”。而在思想史的意义上,马克思早年对政治自由的探索为其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了前提。或者说,正是因为以自由为尺度来界定异化的人本主义批判范式不足以“唤醒”普遍的革命意识,才需要深入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过程中,通过揭露分析资本剥削的政治经济学现象,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提供充足的道义论支撑。因此,就此而言,马克思对政治自由问题的探索是他建立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学说的起点。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3期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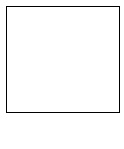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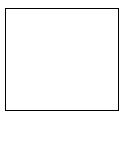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