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15年4月18日,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本文作者严海蓉参加了会议并做了发言。她指出万隆时代有两个遗产,其中更为重要的是第二个遗产:今天反抗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的兴起。如“农民之路”,正是第三世界的、跨国的、反华盛顿共识的农民团体联盟。正如当年的亚非拉人民的团结一样,这样的联盟今天也是跨国的反帝、反资运动。
同样是中国与非洲各国之间的交流会议,希望今天的中非合作论坛继承万隆会议的精神,发扬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独立自主、互助团结的传统,反抗新自由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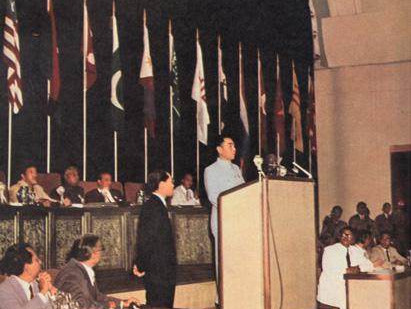
图片来源:网络
2015年4月18日我在杭州参加了万隆会议60周年的纪念研讨会。会议组织者安排我点评津巴布韦的学者萨姆•莫约(Sam Moyo)的发言。
萨姆•莫约是非洲农业研究院(AIAS)创始人,也是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CODESRIA)前主席。他的发言题目为“Thoughts on China’s presence in Africa today”(关于当下中国在非洲的一些思考)。
我和莫约的讨论后来澎湃有报道,网上也有一些转载。因为澎湃报道是基于会上的同声传译整理的,传译过程中不免有简约和疏漏,加上点评时间有限,尽管主持人白永瑞教授已经很照顾,我也没能完全把话说完整。因此,最近把我讨论的内容整理出来。
莫约的发言内容见澎湃的报道: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23594,我非常推荐他2012年的文章:Imperialism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Notes on the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181-203 (帝国主义和原始积累:关于对非洲新掠夺的笔记)。
一
边缘地区、半无产化、原始积累
萨姆·莫约博士在他2012年的文章《帝国主义和原始积累》中提问:什么叫资本的原始积累?原始积累与全球体系是什么关系?文章回顾了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
列宁和卢森堡分析论述的背景是20世纪初欧洲大型垄断企业和国家力量领导的新一轮的殖民扩张和军事化。他们都看到了这一过程中的暴力和超经济手段。不同的是,列宁把对非洲的掠夺看做是垄断资本的结果,认为这将产生最终的不平等发展、战争和革命,但是他也认为这一轮掠夺将同时给边缘地区建立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卢森堡则认为对非洲的掠夺是资本主义内在的需求,资本主义需要通过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占有来解决其自身的消费不足(underconsumption)的问题,对非洲的掠夺重演原始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导致战争升级,直到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解,而这就带来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可持续和终结。
莫约认为历史没有证明他们两位全对,但是他们有三点的确是正确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确成为“最终”的形势;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维度;垄断和原始积累带来无休止的军事化。
继列宁和卢森堡之后,世界体系理论家如萨米尔·阿明等,还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在世界体系中心和边缘有非常不同的剥削方式:边缘地区是原始积累的重灾区;半边缘地区经历了“依附性的工业化”,而资本积累在边缘地区,包括半边缘地区,都有“外向性”,而这种外向性则造成了“半无产化”这一常态特征(“a permanent process of semi-proletarianization”),就是说小生产者被排挤出农村,然而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完全吸收他们。对半无产者的超级剥削——包括没有纳入市场部分的剥削——是对资本的超经济的“贡献”。
莫约认为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总是创造条件维持市场外、没有报酬的劳动,总是寻求把社会再生产的成本转嫁给劳动者本身。也正是这些半无产者在边缘地区成为抵抗原始积累的力量。真实存在的(非教科书里面的)资本主义总是与原始积累相关联,总是与中心-边缘的关系相关联。利润,包括“垄断租”或称为“帝国主义租”,从边缘地区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心地区,使得中心能够有资源延缓其内部的阶级矛盾。然而,现在矛盾和冲突也在中心积累。
二
《新帝国主义》
大卫·哈维的西方中心主义
说起全球化条件下资本积累的问题,这里我想响应莫约对大卫·哈维的批评。大卫·哈维的贡献在于,他把时空关系带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他认为在全球化新自由条件下,资本积累依靠了一种“时空压缩”或“时空修复”(spatial-temporal fix)。在莫约看来,问题在于,在哈维的“时空修复”概念里面,没有中心和边缘的关系,仿佛一切都是流动的,仿佛中心-边缘的关系对于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偶然的,而不是持久的维度。大卫·哈维关于帝国主义论述因此缺少了对中心-边缘关系这一结构性关系和结构性不平等的承认。他在《新帝国主义》这本书里面,倡议现阶段反新自由主义斗争的目标是重建欧美主导的、行善的“帝国主义新政”(a more benevolent ‘New deal’ imperialism),而且认为这场斗争的主战场在美国内部(参见《New Imperialism》,第209-211页)。
莫约从中心-边缘的关系指出哈维的盲点。在我看来,哈维的盲点还包括了无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解体对世界资本主义结构和演变的巨大影响。哈维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他《后现代的条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这本书里已经很明显了。在相对早期的这本书里,他把后现代的条件完全置于西方的内部,几乎完全无视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对于美国二战后三十年(1945-1975)资本主义结构调整的作用,也无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中国与世界体系的接轨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西方资本主义结构再调整、为所谓的后现代性所创造的条件。最终哈维还是在西方内部寻求答案。
三
如何评估中国在非洲?
莫约的寻求不在西方内部,而是在边缘和半边缘地区对世界体系的挑战。他今天有一个尖锐的发问:今天半边缘国家,所谓的新兴市场,本质上是顺从帝国主义的区域稳定力量(subservient regional stabilizer),还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
我的回应分两个部分:我先谈中国在非洲,然后我再谈万隆精神对今天的意义。
在我看来,中国在非洲既是顺从的区域稳定力量,也对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了一定的挑战。中国的工业化既包括了毛时代的自主工业化(今天这部分主要体现为国有资本),也包括了改革开放时代的依附性工业化,即通过引进外资形成的融入全球垄断资本产业链的加工工业。今天被西方看成威胁的是前者。
中国资本“走出去”是八十年代“请进来”在逻辑上的衍生。“请进来”引进大量外资,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使经济外向化。在改革开放20年之际,中国已经资本过剩、产能过剩,资本积累遭遇瓶颈,中国资本便开始“走出去”寻求海外原料和市场。而中国资本走出去,也恰恰是在“华盛顿共识”集团利用非洲国家的债务,胁迫非洲国家进行结构调整,开放投资和贸易、变卖国有资产的时候。所以,西方没有料到的是,“华盛顿共识”也为中国资本进入非洲开了大门,中国资本也成为“华盛顿共识”,成为新自由主义的获益者。比如,赞比亚在1964年独立后,于1969年把殖民者控制的铜矿国有化,然而90年代开始,赞比亚政府便遭遇“华盛顿共识”集团胁迫,逐渐把国有铜矿私有化,中国国企成为收购赞比亚铜矿的外资企业之一。因此,中国资本参与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也是既得利益者。
但中国资本同时在某些局部也挑战了西方垄断资本,按阿明的说法,是给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些回旋的空间。比如,当2008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赞比亚的一些西方铜业公司开始减产、裁员、撤资、甚至关门,大量工人失业。中国国企承诺“三不”,不裁员、不减产、不减投资。中国公司的行为对业界起到了一些压力作用,使得赞比亚政府获得了一点跟其它公司谈判的筹码。津巴布韦土改引发了西方对津实行制裁,津巴布韦的烟草生产从最好时期的240,000吨跌落到40,000吨。2005年在津巴布韦农业生产跌到低谷的时候,中国国有烟草公司进入津巴布韦,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打破了几个烟草巨头对津巴布韦烟草拍卖的垄断,提高了烟草收购价格,有益于振兴津巴布韦的农业;二是加入订单农业的行列,其它公司提供烟草种植农户的贷款收取8-12%的利息,而中国烟草公司提供无息贷款。
总体而言,如果分主次来看的话,主要方面是中国资本在非洲,迎合了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秩序,也是这一秩序的受益者之一,理应承担这一秩序的罪与罚。从次要方面来看,在局部地区、在某些行业,中国资本对西方垄断资本形成了挑战,而这些挑战往往是因为中国资本没有遵从新自由主义的常规,是因为中国资本还需要在某些时候服从政治,这个政治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需要非洲的政治支持(相比较而言,欧美不那么需要、也不那么在乎非洲的政治支持)。
西方主流媒体和精英对中国在非洲有不少并非无辜的误解。西方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兴起于2004年左右,最集中的是美、英、法国,从这些国家流向世界。西方的误解可以分为量和质两个方面。在量方面,夸大中非贸易和投资,中非贸易的确增长迅猛,然而,即便在2011年中非贸易量只占中国和世界贸易量的4%,只占非洲和世界贸易量的13%。在投资方面,中国2003-2011的对外投资占中国GDP的6%;同期,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通常占GDP的12%,世界平均水准为25%;英国和法国的对外投资分别超过其GDP的50%和 40%。2012年中国是非洲第13大投资方。这一误解可能部分地来源于中国人在非洲的数量,人们往往容易看到中国的商贩,然而不容易看到中国商贩对当地贸易的影响远远不及南非在南部非洲国家的连锁超市。在质方面,西方主流常常把中国在非洲的贸易投资定性为“新殖民主义”,这一说法莫约已经进行了驳斥。在我看来,这样的定性是一个话语手段,把中国在非洲的问题特别推出,而且种族化为中国问题或中国人的问题,从而遮蔽和保护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体系。
四
万隆精神在今天
如果我们可以不仅仅提万隆会议,而且可以提万隆时代的话,那么中国在那个时代有一句口号: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在殖民地时期,国家、民族、人民这三个主体的诉求在统一战线里相互共鸣、共振,然而随着万隆时代的到来,随着本土领导者上台,新兴的国家对外面临着如何在帝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寻求立足空间的问题(是否反帝,如何反帝),对内面临着如何处理民族资本与劳工关系、人民与国家官僚的关系问题。这时三个主体的诉求便产生了矛盾,也即在万隆时期的“国家主导的发展”里面,国家、资本、劳工有相互的矛盾。
在万隆时代,中国的道路虽然也有“国家主导发展”的一些特征,但是因为消灭了私人资本,她内部的动力关系与其它新独立的国家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阿明曾经非常犀利地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一口号的内在矛盾来看中国的文革。我们今天对万隆时代的纪念,也应该包括对万隆时代发展模式(national development)的反思、对万隆时代新独立国家处理内外矛盾的反思。
万隆时代在我看来有两个遗产。
遗产之一是今天的金砖国家的兴起。反殖民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万隆时代的亚非拉团结,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积累和对边缘地区剩余价值的吸取,使得新独立国家争取到了发展的空间。这是当年“国家要独立”的斗争所带来的遗产。
遗产之二是今天反抗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的兴起。比如“农民之路”是发源于第三世界的、跨国的、反华盛顿共识集团的农民团体联盟。正如当年的亚非拉人民的团结一样,这样的联盟今天也是跨国的反帝运动,也具有相当反资的性质。这是当年“人民要革命”的遗产和延生。
今天对批判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需要发扬哪一个遗产?在我看来,应该是后一种。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