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世纪70年代末,农村土地改革以及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开始向全国推行,中国农村开始了又一次植根于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与之相应地,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乡村的文学叙述建立起了一种关于自己为自己劳动的“小生产者的梦想”的乡村想象。而这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矛盾也凸显出来: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和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编者注:两篇小说链接附在文末】是这一转变的代表。
《鲁班的子孙》呈现了社会主义伦理道德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的冲突;《腊月·正月》实际上则可以被看作是对《鲁班的子孙》的回应与改写。在《腊月·正月》的叙述中,乡村传统伦理道德与资本逻辑之间的冲突逐渐退场,“发展主义”和市场逻辑的合法性在文本内部得到了逐步的无意识的确立。这也昭示着随着现代化转型的推进,乡村完全被纳入城市化的轨道,农民亦被纳入城市的轨迹成为边缘群体,而这也正是20世纪90年代乡村和农民故事的开端和起源之一,从中得以窥见这一历史时期乡村与农民的命运。
6月2号晚上,本文作者戴哲老师将做客诚食讲座。本次讲座,戴老师通过《陈奂生上城》这篇小说继续为大家分析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乡村故事,详细讲座介绍不日将在本号推送,敬请期待。
作者|戴哲,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究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研究。
责编|律成非文
后台编辑|童话
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土地改革,以及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实行,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乡村的文学叙述建构起来的实际上是一种关于自己为自己劳动的“小生产者的梦想”的乡村想象。这样的一种乡村想象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早期乡村写作的叙述逻辑,其实也是当时整个社会对于生活和世界的一种总体性的构想。对此,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何士光的《乡场上》这三个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文本极具代表性。[1](参见《戴哲:饥饿、财产、尊严与小生产者的梦想——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乡村故事》一文)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一乡村想象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内在包含的非现代生活方式与现代化追求之间的矛盾也凸显出来,对此,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和贾平凹的《腊月·正月》是值得被讨论的两个文本,前者将矛盾具体化,而在后者的叙述中矛盾得以逐渐消解。这两个文本虽然有着极为相似的叙事结构和情节——关于“老年”和“青年”的冲突,但在叙事逻辑上却全然不同。
王润滋通过《鲁班的子孙》发现了与改革的表面进程不相协调的东西,并塑造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作为经济人的青年农民形象,从而让具体的问题得以被讨论——改革/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理想能否兼而有之,传统伦理道德与市场逻辑能否并行不悖?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必须面对的难题和矛盾,只不过他又在虚构的文本内部想象性地和解了这些问题。
而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则宣告了“老实人”陈奂生或者说代表着“良心”的老木匠的彻底退场。虽然贾平凹也极为生动地表现了传统伦理道德与经济发展/市场逻辑之间的冲突,但最后却巧妙地对冲突进行了化解,使我们看到乡村如何被纳入现代化的轨迹,“市场逻辑”、“发展主义”在文本内部如何得到了逐步的无意识的确立,这种“纳入”和“确立”一定程度上是以破坏乡村的传统秩序为代价的,而这也正是20世纪90年代农民和乡村故事的起源所在。
一
小木匠的“返乡”:作为“成功者”的闯入
如果说早在建国初期以城市为经济发展重心的现代化思维还只是一种“有选择的现代化”——即在生产力、工业化和科技水平方面对城市进行肯定,而在生活方式、伦理道德、文化价值和审美意识方面却对城市带有天然的偏见和歧视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城市不仅仅在物质定向方面得到认同、成为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标识,而且在精神定向方面也成为具有优势导向的力量。由此可以想见,城市及其表征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对传统的乡村和农民进行改造。
在此意义上,对于王润滋创作的《鲁班的子孙》,其故事的真正展开应当始于小木匠的“返乡”。小木匠的“返乡”某种程度上宣告了“城市”将以一种异常强硬的姿态出现在乡村面前,从而对乡村的传统秩序结构产生破坏。换言之,《鲁班的子孙》实际上可以被复述为一个来自强势空间/城市的闯入者,试图改变甚至破坏原有空间的故事,“闯入者”小木匠以一种“异己”的形象出现在小说中,他一定会被传统的乡里空间所排斥,而这个传统的乡里空间的代言人显然是老木匠。所以,老木匠与小木匠的冲突成为整个故事的核心。
那么,闯入者/小木匠是如何闯入到乡村这个空间的,或者说,城市是如何进入到乡村世界的呢?显然小木匠是以“成功者”的形象出现在黄家沟的,并试图以城市所表征的“知识”对其进行“改造”。
小木匠作为“成功者”的形象最先通过“物质”得以凸显。不仅是小木匠返乡时气派的衣着,“大翻领的蓝涤卡制服棉袄,新锃锃的呢料鸭舌帽,腕子上的手表闪着亮光……”[2]还有小说提及的小木匠从城市带回来的“大提包”,当小木匠一件件地将大提包里的“宝贝”拿出来,似乎在一遍遍宣告自己的“成功”。大提包里不仅装着给爹的皮货料子做的袄,还有处理胶鞋、尼龙袜、花枕巾、帽子、围脖儿等。显然,中国农民与本雅明和波德莱尔笔下漫游者进入城市的方式截然不同,前者通过对现代的某种物质的身体感觉进入城市,这显然是一种第三世界进入城市的路径。
这样的一种“进城方式”,早在晚清以后便已经开始。可追溯至茅盾的《子夜》中的吴老太爷进城。从未到过城市的吴老太爷一入到城市的空间,便被城市疯跑的汽车、闪烁的霓虹灯、高耸入云的摩天高楼吓得没了知觉[3];以对“现代物质”的身体感知进城的方式在1980年代初期的《陈奂生上城》中也有所体现,陈奂生在招待所醒来时发觉自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房里的一切,都新堂堂、亮澄澄,平顶(天花板)白得耀眼,……再看床上,垫的是花床单,盖的是新被子,雪白的被底,崭新的稠面,刮刮叫三层新”[4],这一切让陈奂生无所适从。
吴老太爷与陈奂生都因为城市的“现代物质”感觉结构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小木匠对于“现代物质”的感觉全然不同,他因为拥有了来自于城市的“现代物质”,以“成功者”的形象回到了黄家沟。可是即便如此,小木匠却与吴老太爷、陈奂生一样让我们看到,城市凌驾于农村之上,农民成为理所当然的他者,这也再次证明了城市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异常强硬的存在。
相比之以“物质”凸显的成功,作为“成功者”的小木匠的“成功史”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小木匠如何成功的更为关键。虽然王润滋创造了一个作为物质成功的“成功者”的农民形象,不过显然王润滋的目的并不在于讲述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是借由对这个“成功者”的叙述来揭示某些问题,如经济发展与传统乡村伦理的矛盾,因此《鲁班的子孙》的叙事模式其实可被称为“闯入/破坏”模式。
小木匠当然也有过一段血泪史,王润滋在小说中告诉我们,小木匠刚到城里时做过临时工,睡过澡堂。可是当小木匠再次回到黄家沟时,穿得极其体面,还有专车接送,这一切来自于“林局长”的照顾,“俺在城里有靠山……林局长,硬着呢!”[5]这句话道出了小木匠成功的秘诀——“官商勾结”或者“资本与权力的结合”,这几乎也涉及到了20世纪80年代市场化的某种秘密所在:市场化背后其实是权势的操纵。
林局长为什么会帮小木匠,根本原因当然不在于小木匠有很好的手艺,而在于小木匠用很好的手艺免费给林局长女儿打了三套家具。这里也涉及到另一个新的概念——权力寻租,权力自身不可能产生利润,所以它必定要找一个对象,通过对这个对象的介入而获取利益。所以,林局长与小木匠之间是一种双赢的关系。
于是小说中关于老木匠端详小木匠的“手”的细节具有了某种反讽的意义,“这哪里像一只小伙子的手:又粗又短的手指,简直像一排磨秃的石钻……手掌几乎全是一块硬茧;拇指让锤头或斧顶打过,指甲死去了,只留下难看的一团肉”[6]。老木匠以小木匠粗糙的双手打消了对小木匠成功的怀疑,并认定小木匠的钱是通过自己的双手赚来的,这显然是对劳动重要性的强调。但正如小木匠的钱是通过与林局长的合谋赚来的,那么这一关于“手”的细节描写反而质疑了劳动的正当性。换言之,在《鲁班的子孙》中不仅是个人劳动,甚至是劳动本身的合法性也被消解了。
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官商勾结或权力寻租这一现象会最先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原因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阶级斗争结束”[7],阶级斗争的停止实际上得益的是特权阶层;另一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对改革和实践的强调。
自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实践论”极大解放了当时中国上层到下层的想象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此,一种最高的价值观、世界观[8]被悬置起来。虽然“悬置”有利于经济发展,却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这一被“悬置”的部分逐渐被遗忘,一种世俗性的对财富的追求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以林局长和小木匠实现了“合作共赢”。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小木匠与老木匠接受的关于如何成功的知识迥然不同。小木匠接受的是市场化的训练,而这一“市场化的训练”却并不来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9],而是来自“官商勾结”、来自不惜一切手段只求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益的原则——这也是资本的逻辑;而老木匠坚持的“良心”则表征着集体主义时代的理想和传统。因而不同的知识构成了不同的主体性,从而建构起不同的主体,二者之间有一个逻辑关系。也正是因为这样,福柯才特别强调知识考古,他认为主体并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由知识形成的,但是当它碰到另一种“新的知识”时,便又会形成另一种新的主体。
也就是说,当经过市场训练的“成功者”小木匠携带一种“新的知识”重新回到/闯入乡村时,实际上他要解构的是整个乡村秩序和传统[10]。所以其实可以将小木匠看作是市场化力量的隐喻,这种市场化的力量企图把乡村纳入自己的逻辑里面,而这个逻辑在小说中的表现则是小木匠要重新开一个木匠铺,具体则是通过“价目表”和“拒绝富宽”这两个细节被表述出来。
二
“价目牌”和“拒绝富宽”:
乡村共同体的破坏及其道德困境
在《鲁班的子孙》中,小木匠将木匠铺从“黄家沟木匠铺”更名为“黄记木匠铺”,并在招牌上印上“为您服务”四个大字,而不是“为人民服务”,这种更改本身就饶有意味——象征着老木匠所代表的“集体时代”的结束,“个人时代”的到来。当然,对此“黄记木匠铺”的“价目表”则表现得更加具体,价目表上大到250元的大衣橱,小到0.2元打撅孔都明码标价。这种“明码标价”无疑让整个黄家沟,让老木匠及其所代表的集体主义时代的“良心”受到了巨大冲击。但实际上这样的价目表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小木匠是以利润为目的的,所以小木匠一定要精打细算,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低投入、高产出”。
正是在此意义上,《鲁班的子孙》才有了另一个值得被讨论的细节即“拒绝富宽”。正是因为需要“低投入、高产出”,小木匠才会宁肯让自己的妹妹来木匠铺干活,也不愿意接受富宽入伙,这完全遵循的是资本的逻辑。在这个逻辑面前,所谓的熟人社会的“人情”一定是要被排除出去的,因为当所有的行为都转化为一种价格时,那么“人情”也必然会被以“金钱”来衡量。
所以,面对富宽,虽然小木匠也心软过,但最终还是非常坚决和干脆地拒绝了富宽加入木匠铺。因为他计算出如果让富宽进木匠铺,自己的损失一定很大,正如他对富宽所说“富宽大叔,你要进了木匠铺,往后的账谁能算得开?要真像俺爹说的那样去分,荒算你一年要分走俺八千块!八千块能买多少木料?能做多少家具?里外里又能赚回来多少钱?”[11]
也就是说,在金钱面前,所谓的“面子”、“人情”根本不足一提,它们甚至成为被嘲讽的对象,而抛弃对“面子”的顾虑似乎成为一个人成功的最基本的条件。但实际上,面子或人情表达了很多层面的内容,比如良心、尊严、尊重等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虚伪,它也是传统的乡村共同体得以形成和存在的重要条件。所以,当以小木匠为代表的资本逻辑突破了乡村的最后防线:面子和人情之后,必将导致乡村共同体的最终破裂。
当然,小说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结尾。有评论者说:“小说以老木匠对于‘良心’的满怀自信而告结尾,老木匠与小木匠的冲突在文本内部达成和解,但是这种和解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出现。”[12]所以,小说现有的结尾便显得特别有意思——小木匠在老木匠代表的传统和道德压力面前最后又离开了黄家沟,但是,当女儿秀枝问他:“俺哥还能回来么?”时,老木匠笑着说:“傻孩子,不回来他能上哪儿去?别看天底下这么大,离了黄家沟,没他立脚的地场!”[13]老木匠不仅在安慰女儿,其实也是在安慰自己。
小木匠肯定不会再回到黄家沟,因为离开了黄家沟,他可以活得更好,这就是后来的“乡下人进城”和农民工的故事。[14]就连王润滋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写作了一篇关于“农民工”的小说——《残桥》[15],从而某种意义上对老木匠在小说结尾处的预言进行了回应:《残桥》中的农民德兴如小木匠般义无反顾要离开乡村去往城市,但是他在城市干的其实是苦力活,忍受着高强度剥削。可即便如此德兴仍然不愿回去,因为在乡村更无法生存。
在度过了短暂的黄金期之后,1984年后,农村产品开始供大于求,“卖粮难”问题出现,而此时改革的重心已经开始转移到城市,到后来乡镇企业也无法维系下去,大批农民为了生计不得不走向城市[16]。正如张抗抗的《芝麻》[17]中,保姆芝麻宁愿在城里每三个月花五十块做孕检,也不愿意回到乡村,因为在城里一个月可以赚五百块,没有这五百块全家人就没好日子过,所以算来算去到城里打工比在老家呆着强多了。严海蓉在《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中也曾说道:“在中国当代发展的情境下,农村成为她们想要挣脱和逃离的生死场,而不是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空间、做‘人’的空间是城市。”[18]
老木匠和小木匠之间的故事已不仅是乡村共同体内部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被完全纳入到现代化的过程中,小木匠的出走意味着个人完全可以退出,也不得不退出共同体,而整个乡村也将被纳入城市化轨道。于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向城市,乡村开始空壳化。
实际上,与其说《鲁班的子孙》讨论的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倒不如说它面临的是政治经济层面的问题。小木匠的木匠铺之所以要摧毁亲情和人情其实都源自于利益的驱使,而与利益相关的一个最核心的概念是“剥削”。但是,在小说中这个概念并未真正出现。
小木匠在考虑是否要拒绝富宽时,曾思考过雇他当临时工:“要是照城里雇临时工的价码,那倒合理,国家规定顶高一天一块七角六,满打满算一年给你八百块。八百块,不少个数儿了,你到哪里去挣?”[19]但是,他接着想到,“可是,人家要是说俺雇工剥削呢?其实啥剥削,国家能雇,私人就不能雇,人家日本、美国开大工厂都是雇人,爱雇谁就雇谁,自由着呢!不过眼时还不能出这个头儿……”[20]这段话是《鲁班的子孙》唯一一处出现剥削的地方,但又被王润滋以小木匠“不能出这个头儿”压抑。可是压抑并不代表消灭,更何况小木匠不雇富宽并不是出于良心,而是不想“先出这个头儿”。
理论上与之相关的讨论有过不少,比如以农民陈志雄雇工承包鱼塘算不算剥削这个由头在1981年5月到8月的《人民日报》引发了历时三个月的大讨论。虽然中央1980年代中央75号文件已明确规定“不准雇工”,但最后这场讨论以佘大奴、黄克义的《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中给出的结论告终,“陈可以跨队承包,也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
并且,对于雇工问题,邓小平在1984年10月22日明确指出可以放两年再看。到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对“雇工”问题再一次发表了看法:“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损害了对我们不利。”[21]由此“雇工”获得了充分的合法性,并最终被命名为“私营经济”[22]。
也就是说,改革和发展这两个概念一定会阻碍剥削这一概念的出现,因此王润滋将《鲁班的子孙》叙述成了一个关于“良心”(道德)的故事,从而也导致了叙事上的局限性[23]。虽然如此,王润滋的矛盾和困惑却难能可贵,因为他至少触及并一定程度上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24]。尤其是在改革进程中,乡村和农民的处境。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即使99%的农民都富有了,还有百分之一在受苦,我们的文学也应该关注他们,我的同情永远都在生活底层的受苦人。”[25]但是,正如同“雇工是不是剥削”的讨论的终结一样,《鲁班的子孙》中的“道德的困惑”也都不再是问题。因为在改革这一强大的逻辑面前,所有的阻碍都将自行消失。所以,在关于《鲁班的子孙》引发的争论结束后,非但再没有类似的文本出现,反倒是出现了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叙述,比如贾平凹的《腊月·正月》。
三
有“良心”的王才:
道德形象的反转与改革逻辑的确立
与《鲁班的子孙》一样,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同样讲述了一个老年和青年之间的冲突故事。老年韩玄子与老木匠黄志亮一样代表了乡村的传统与权威;而青年王才则与小木匠黄秀川有着某种相似性:小木匠开了自己的木匠铺,而王才则办起了自己的加工厂。与小木匠对老木匠的冲击一样,王才与韩玄子之间也产生了极大的冲突。
虽然《腊月·正月》与《鲁班的子孙》在主题和结构上如此接近,但实际上两个文本有着完全相反的叙事逻辑和价值取向。如果说在《鲁班的子孙》中,王润滋偏向的是老木匠的话,那么在《腊月·正月》中,贾平凹则完全偏向了王才。显然,当面对现代化这一极其强大的逻辑时,所有的阻碍都必将自行消失,无论是道德的困惑还是关于“雇工是不是剥削”的讨论都不再可能出现。甚至于老木匠所代表的“良心”也被移花接木到了青年王才身上。换言之,在《腊月·正月》中,我们会看到“先富起来”如何在文化和道德上确立了自己的合法性。正是在此意义上《腊月·正月》推翻甚至终结了《鲁班的子孙》的困惑和思考。
当然,贾平凹在自身的创作过程中也经历过纠结与困惑。在创作《腊月·正月》之前,贾平凹写过《小月前本》和《鸡窝洼的人家》,三者被合称为农村改革三部曲。在《小月前本》和《鸡窝洼的人家》中,贾平凹在呈现了改革的巨大能量及其遭遇的阻碍时,表现出他对于改革逻辑与传统乡村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思考,甚至是对于改革逻辑/经济人伦理的犹疑和纠结。所以无论是《小月前本》中的门门与《鸡窝洼的人家》中的禾禾,虽然都与王才一样认同和遵循经济理性和现代逻辑,但贾平凹却并没有让他们在乡村世界确立起完全的合法性,而是重点呈现了他们与乡村秩序结构的冲突。所以,相对于《腊月·正月》,《小月前本》与《鸡窝洼的人家》其实更具复杂性。
《腊月·正月》某种意义上终结了贾平凹自身在《小月前本》与《鸡窝洼的人家》中的犹疑与思考,从他将青年与青年之间的冲突:《小月前本》中的门门与才才,《鸡窝洼的人家》禾禾与回回置换为青年(王才)与老年(韩玄子)之间的冲突便可见一斑。至少在《小月前本》与《鸡窝洼的人家》中,我们还可见青年与青年之间的势均力敌,但是在《腊月·正月》中,青年王才对老年韩玄子实现了全方位碾压。贾平凹的纠结与困惑的消失某种程度上论证了现代化、市场逻辑的强大。
当然,比之贾平凹自身写作态度的转变,经由《腊月·正月》与《鲁班的子孙》这两篇主题结构极为相似,却写作时间不同,叙事逻辑和价值取向完全相反的小说,更可见“改革”与“发展”的势不可挡。《腊月·正月》对王润滋困惑的推翻和终结主要通过对老木匠和小木匠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改写被表述出来。虽然如老木匠一样,韩玄子一直以来享有较高的声望,村里每个人都要敬他几分。但在韩玄子身上,老木匠最重要的一样东西“良心”或“德性”被抽离,反倒是他“善嫉妒、爱报复、仗势欺人”的形象在小说中逐渐凸显出来,而他所具有的威望和所受的尊重也开始逐渐消失。最后,这些威望和尊重全部被贾平凹赋予了王才。
无疑,贾平凹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王润滋的颠覆——老年与青年的冲突,被改写成老年对青年的压制,并且这种压制被叙述成不可理喻甚至是卑鄙的。很显然,贾平凹的倾向性比王润滋明确了许多,所以,他一定会给出一个肯定而清晰的结尾——青年/王才,战胜了老年/韩玄子,青年所代表的现代化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得以确立。
韩玄子“善嫉妒、爱报复、仗势欺人”的形象通过几个事件被表述出来。首先是“公房事件”。听说生产队决定将四件空置的公房卖掉,王才欲买下之用来扩大作坊,于是特意去征求韩玄子的意见,韩玄子却盘算好自己将公房买过来。所以作为公社干部,他出了个以抓纸蛋儿来决定谁有资格买公房的主意。有意思的是,村里的一个完全买不起公房的无赖气管炎得到了这个名额。于是韩玄子想尽办法将名额从气管炎那里要了过来,可又因为儿子不同意建房,不得不让二贝负责将名额再转让出去。让二贝转让的时候,韩玄子一再叮嘱名额一定不能落到王才手上。
另一个事件是“告状”。王才因为要扩大加工厂,所以将地租给狗剩耕种,韩玄子知道后,便在公社王书记面前说王才搞资本主义的一套,要求公社出面治治他。
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是韩玄子给女儿叶子“送路”,也即为女儿办结婚酒席。韩玄子声势浩大,准备宴请村里所有的人,但惟独没有通知王才以及与王才站在一边的秃子和狗剩。显然,韩玄子将所有的赌注压在了这次请客上,试图借此挽回自己的面子和地位,彻底打垮王才。
可是结果如何呢?王才不仅得到了公房的名额,而且公社书记也告诉韩玄子公社方面不方便出面干涉王才办加工厂。而韩玄子抱以最大希望的请客也以失败告终,因为请客的当天,县委马书记竟然亲自给王才去拜年,韩玄子家显得门庭冷落。所以,虽然小说一开头便告诉我们韩玄子在村里的地位颇高,但实际上小说最后让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见不得他人比自己好、仗势欺人的可鄙的老人形象。
更有意思的是,韩玄子一直针对的王才,在小说中却只是以韩玄子的“假想敌”的身份出现,韩玄子的“对抗”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因为王才根本从未想过要与韩玄子对抗,甚至还处处尊重韩玄子,这对韩玄子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所以,相对于韩玄子,王才的形象无疑是高大的。
首先,小说为王才设置了一个“转变”的情节。王才从前是一个样样不如人的农民,可是在土地承包后,王才通过自己的勤劳办起了加工厂,并且越来越富有。此叙述可谓两全其美,既肯定了乡村改革的合法性,又重新确认了“个人劳动”的正当性,从而弥合了小木匠身上的不完美,为改革扫清了障碍。但是当中国的乡村改革被组织进欲望的叙事中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对劳动的质疑,市场化的逻辑一定会将“劳动”排除出去。虽如此市场却仍需要同时编造“劳动致富”的神话,某种程度上,《腊月·正月》对王才形象的塑造也莫不基于此目的。
与此同时,小说还告诉我们,虽然自己有钱了,王才却不曾忘记村里的人。小说提及王才还是一个处处为村民着想的人。自从办了加工厂,收入一天天多起来,可是王才的人缘却似乎有所下降,对此王才也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他并没有为此报复村里的人,而是不断地反省自己是否亏待过乡亲们。当村里需要钱时,他也毫不吝啬,主动提出一年一度的办社火的资金由他来负责,并且要求不留名。经由这样的叙述,老木匠的“良心”似乎被转移到了王才身上——所以,王才不仅是一个勤劳的人,还是一个发家不忘他人的有良心的人。[26]尤其是当我们读到韩玄子请客故意不请王才,而王才却单纯地认为既然请全村的人,没有理由会不请他时,我们几欲将所有的同情和尊重都赋予他。到此,王才的“先富起来”在情感和伦理上获得了合法性。
所以,借由对韩玄子、王才的性格呈现,贾平凹完全反转了老木匠与小木匠两个形象。在他的笔下,老木匠变成自私的、嫉妒心极强的、为保住个人地位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压制年轻人的韩玄子,而曾经在《鲁班的子孙》中冷酷的,不顾亲情、人情的小木匠则变成有良心的人——王才。
贾平凹的意图已非常明显,他不仅让我们看到“先富起来”如何在情感和伦理上获得了其合法性,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在乡土世界中重新树立自己的地位或者说重构另一种乡村世界的地位所需要具备的条件,这种地位不同于韩玄子曾经所拥有的地位,而是一种由“经济实力”所建构起来的势力和威性。通过文本的脉络可以看到,王才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关键在于“县委马书记给王才拜年”这一情节。拜年本身当然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马书记的登门意味着对王才的肯定,他亲口对王才说:“是要谢谢你!全县有条件的都来学你。不要说几百户、几千户、就是十几户,那也会了不起的!”[27]
马书记的肯定意味着“先富起来”也获得了政治上的支持[28],这毋宁是最根本也最有力的支持。所以,当听到王才说加工厂现在是十八人时,马书记表示可以再增加,由此可见,“雇工算不算剥削”显然已不是问题。那么,王才的加工厂获得马书记的肯定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王才的“良心”吗?显然不是,王才的加工厂之所以会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一定是因为经济效益,正如狗剩在王才家面对众人大声说的:“眼下在这镇子上,最有钱的是谁?王才!最有势的是谁?还不是王才?!”[29]也就是说,有钱与有势之间被一种因果关系联接起来。
所以,王才通过自己的经济实力重构了所谓的乡村世界的权威,于是衡量成功的标准逐渐被固定化和单一化起来,财富或经济成为唯一的标准——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的问题之所在。如王晓明所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被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笼罩:即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社会滑进了以“效益”为基本曲线的“发展”轨道……对眼前效益开始热烈追求,而对其它非实用的事物的排斥”[30]。
这一“新的意识形态”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王才”的故事中早已初见端倪。而经由王才的成功,也可见最早的发展主义的起源——诚然,“对发展的追求一直是毛泽东的现代性方案的内在品质之一,但是在社会主义的经典话语表述中它只是达到更高乌托邦理想目标的权益手段,而且这套话语事实上也是把国内的平等理想(消除三大差别)与解放全球、人类大同的普世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诉求”[31]。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发展的追求已经衍化为发展主义,发展开始成为发展的目的自身,成为最大的意识形态,也成为社会主义‘卡理斯玛’解魅之后‘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它也不再提出资本主义秩序之外的普世主义,而是认可这一秩序的基本法则并试图融入其中”[32]。
因此,即使王才再有“良心”,他也不可能按照老木匠经营木匠铺的方式来经营加工厂,这种叙述无论如何不可能出现在小说中。王才的加工厂有一套现代的管理理念,正如加工厂的狗剩所说:“他当了厂长,说要科学管理,定了制度,有操作的制度,有卫生的制度,谁要不按他的要求,做的不合质量,他就解雇谁!现在是一班,等作坊扩大收拾好,就实行两班倒。上下班都有时间,升子大的大钟表都挂在墙上了!”[33]
这一段文字实际上正象征着王才对未来的想象,这明显是一种西方式的、极为现代的想象,这种想象与小木匠的“黄记木匠铺”具有某种同构性,依赖“机器”生产,以“利润”作为保障和目的,所以也一定要排除“人情”这个概念。因此,当气管炎也想进加工厂上班时,王才果断拒绝了,因为他不符合王才对“员工”的要求;当他得知狗剩与秃子在巩德胜店里闹事后,勒令二人以三倍的价钱赔偿巩德胜的损失——此乃对人员的“管理”。
当然,这部分内容在小说中被轻描淡写地略过了,一方面原因在于其可能会与王才“有人情味儿”的形象产生冲突;另一方面按照小说的逻辑或者“发展的逻辑”,这些问题并不是问题,而是“自然而然之事”。所以,被赋予了老木匠式的美德的王才最终必然要破坏传统的乡村秩序。因为在贾平凹看来,老木匠所表征的德性传统实际上已经成为经济的附庸,它们被降低到实用的层面。某种程度上,不止是贾平凹,这是这个时代大多数作家的“改革共识”,哪怕这种共识只是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出现。
在贾平凹的《腊月·正月》之后出现的高晓声的《送田》[34],某种意义上对理性经济人王才必然要破坏传统的乡村秩序予以了展开。《送田》讲述了与王才一样凭借“经济实力”成为村庄中的“权威”的周锡林,如何利用和抛弃土地的故事。这个故事再次让我们看到,乡村如何被彻底纳入现代化轨迹,作为现代化核心的“发展主义”如何确立起合法性,并如何对传统的乡村秩序结构进行破坏。对于“改革”和“发展”的强烈呼喊,必然要求类似王润滋式的困惑立即终止。正如“我们不应老是站在‘昨天’那里,以低沉、哀怨的笔调叙述一些‘昨天’的故事,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子,满腔热忱地走进‘今天’的生活激流中来。熟悉今天,认识今天,理解今天,透过一切错综复杂的现象,触摸到它的本质,它的脉搏,并且把握它的历史进程。”[35]
四
结语
如果说,从《腊月·正月》得见改革的本质是经济发展,那么又该如何来回答《鲁班的子孙》留下的问题——什么是明天的故事?虽然王润滋认为明天的故事是现代经济的发展与乡村传统秩序结构的兼而有之,可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幻觉。而《腊月·正月》中依靠“经济实力”重构了乡村世界的威信的王才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它所能带来的显然不可能是《乡场上》《李顺大造屋》所建构的“小生产者的故事”,反倒是对乡村伦理道德秩序的冲击以及对农民情感结构的改造。
如果将1980年代不同时期的几个典型文本进行串联:比如1980年代初期建构了“小生产者梦想”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乡场上》《李顺大造屋》,在1980年代初期症候性地表达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冲突的《陈奂生上城》,以及1980年代中后期呈现了乡村改革与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矛盾的《鲁班的子孙》,乃至确立了市场逻辑合法性的《腊月·正月》,一条完整而清晰的叙事脉络便得以呈现。
经由这条叙事脉络,得以见到改革进程中,乡村传统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乡村传统秩序结构如何退场,农民如何被纳入城市的轨迹成为边缘群体,而这也正是1990年代乡村和农民故事的开端和起源之一。
注释:
[1]对此戴哲:《饥饿、财产、尊严与小生产者的梦想——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乡村故事》,《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第176页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展开。
[2]王润滋:《鲁班的子孙》,选自《自己的日子》,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3]茅盾:《子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4]张春波编:《陈奂生上城》,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页。
[5]王润滋:《鲁班的子孙》,选自《自己的日子》,第125页。
[6]王润滋:《鲁班的子孙》,选自《自己的日子》,第131页。
[7]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8]这里的“最高的价值观、世界观”实际上可等同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
[9]此处意在说明市场经济本来不是不好的,但是因为权力对市场的操控,导致1980年代直至当下的市场化变得非常糟糕。
[10]乡村的主体由乡村传统和秩序构成,而小木匠所带来的新的知识其实是一种“现代知识”,这种知识肯定会破坏乡村传统秩序结构,但问题是这种新的知识又无法建构一种新的传统,所以乡村便失去了主体性,完全依附于城市,这也正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的处境和问题。
[11]王润滋:《鲁班的子孙》,选自《自己的日子》,第146页。
[12]林凌:《文学中的财富书——新时期文学写作演变的再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96页。
[13]王润滋:《鲁班的子孙》,选自《自己的日子》,第169页。
[14]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已经出现了不少书写个人从共同体退出,走向城市的作品。比如田中禾1984年创作的《五月》、何士光1987年创作的《苦寒行》、打工作家张伟明1989年创作的《我们INT》等。如果说前两篇小说还只是略有涉及“到城里去”的话题的话,那么《我们INT》已经是在讲“打工者”(农民工)的故事了。
[15]王润滋:《残桥》,《中国作家》1986年第6期,第4页。
[16]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农村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4年,这一时间段由于农村改革的推行,农业增产增收很快,可以视为农村的“黄金期”,第二个阶段是1985—1988年,这一阶段农业出现徘徊,但是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所以问题还不是很大,第三个阶段是1989—1991年,农民收入出现停滞,这与政策开始偏向城市以及乡镇企业的诸多问题开始显现有关,所以从90年代初开始“民工潮”出现。
[17]张抗抗:《鸟兽还是善飞:张抗抗近年中短篇小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93-138页。
[18]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读书》2005年第7期,第74页。
[19]王润滋:《鲁班的子孙》,选自《自己的日子》,第146页。
[20]王润滋:《鲁班的子孙》,选自《自己的日子》,第146页。
[21]关于此次讨论,在《共和国辞典:感受隐秘的当代史脉搏》中有详细的记载,此处的相关材料都来源于此记载。网址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8811647。
[22]在讨论中,经济学家林子力提出“七上八下”的标准:8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可是这一标准终被破除,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私营经济”的提法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根本大法中。
[23]这让我想起主旋律小说。主旋律小说以“大和解”的叙事策略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形成共谋和契约:既在小说的叙事空间中触及了具体的社会问题,又在虚构的文本内部解决了这些问题;与此同时,它并不触动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基础,反而是巩固了上层建筑。但显然《鲁班的子孙》的大和解与主旋律小说的“大和解”并非一回事,而我所说的王润滋叙事上的“局限性”也并不是说他为了迎合“改革”的意识形态而特意将一个本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归结为道德的问题,而是说在当时的语境下,作家无法展开讨论,也就是说是时代的限制导致了《鲁班的子孙》的局限性。
[24]其实在《鲁班的子孙》中除了“剥削”问题,还涉及了另一个相关的问题——“公平”,或者说“分配”——比如老木匠说自己辛苦了一辈子也没有发财,老实人富宽却生活困难,但是小木匠轻而易举就可以赚到“两千块”。这正是王润滋在创作谈中所说的:“一部分农民富起来了,可是那些没有富起来的怎么办?”八十年代初《中国青年报》就公平问题也曾展开过一次讨论,其核心问题是:我们应该追求结果平等还是起点平等?最后讨论以“起点平等比结果平等更重要”的结论告终。所以,自此以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似乎成为国策,甚至公平被放在了和效率相对立的位置上,似乎是,只要公平多了,效率肯定就要降低。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内容的价值观悬置,强调“实践”之后,却无法处理“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关系。所以1990年代以来才会有愈来愈严重的贫富差距和越来越明显的阶层分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很多问题其实都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
[25]王润滋:《从〈鲁班的子孙〉谈起——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山东文学》1984年第11期,第67页。
[26]王才依靠勤劳致富并且还不失掉“良心”的这一形象很容易让人想到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安在小说中也被塑造成一个有“良心”的个体户。他贷款一万元将砖厂扩大,为的是可以解决一些村民的困难,让他们可以来厂里干活,但此次“扩大”以失败告终。这个时候村民并不念孙少安曾经的好、也不顾及他现在的困难,只管向他要入股时交的钱。孙少安曾一度一蹶不振,但是最终坚持了下来,砖厂死灰复燃,并且效益越来越好,这个时候他不计前嫌又让穷困的乡亲再来厂里干活,好让他们赚几个买化肥的钱。所以最后孙少安成为整个乡最有声望的农民企业家。表面上孙少安与王才非常相似,但实际上二者有着根本区别。与贾平凹不同,路遥对孙少安这一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是想重新塑造“劳动是美德”的这一观念,劳动成为美德,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的关键。所以,他会在小说中塑造另外一个“个体户”形象——田海民。田海民虽然也是靠自己办起了鱼塘,可是他却非常“精明”,连自己的父亲和四爸想要入股,他都没有同意,即使两位老人只是想干点粗活笨活。而村里有些穷家薄业的人想借几个急用钱,谁也不会去找田海民,因为他不会同意。所以,田海民在村里不受欢迎,但是他和妻子田银花对村民们的攻击很不理解:“我们有钱,是我们自己用劳动和本事赚的,又不是偷的抢的,外人有什么权利说三道四?”显然小说要告诉我们的是:财富一定是要和“良心”结合在一起的,劳动应该成为美德。但是这种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显然发生了变化,劳动成为发家致富的手段。而王才尽管被赋予了“良心”,但实际上这里的良心已经被降低到“实用”的层面,是为了论证王才“财富”的合法而存在,已经成为“经济”的附庸。这样的结论通过贾平凹将在乡村有着长老式权威的“韩玄子”这个老人塑造成嫉妒心极强,并试图凭借自己的“声望”报复甚至陷害王才的小人形象得以见出。
[27]贾平凹、吴义勤:《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腊月·正月》,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24页。
[28]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该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再次提出了“先富”的思想,当时的提法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1985年、1986年间邓小平在多个场合曾公开表述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29]贾平凹、吴义勤:《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腊月·正月》,第127页。
[30]参见王晓明:《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天涯》2000年第6期,第10页。
[31]刘复生:《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第47页。
[32]刘复生:《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第48页。
[33]贾平凹、吴义勤:《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腊月·正月》,第66页。
[34]高晓声:《高晓声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76-86页。
[35]孙健忠:《如何深刻反映农村生活?——在长沙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纪要》,《文艺报》1981年第1期。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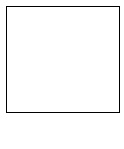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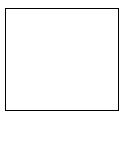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